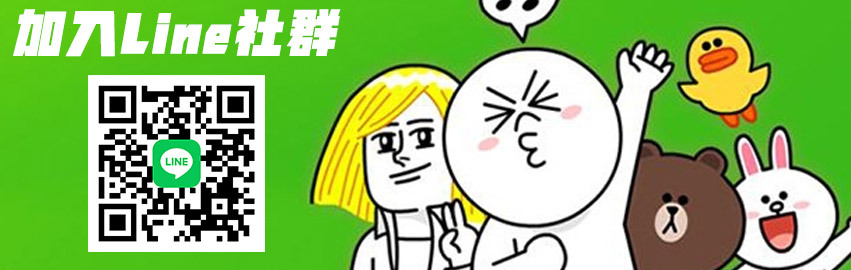作者:LukaszMankowski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AsianMoviePulse
(2024年3月27日)
從電影生涯伊始,是枝裕和就以家庭主題的影片而聞名——這與最受西方影評人欣賞的日本電影大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小津安二郎。
早在1995年的銀幕首作《幻之光》中,是枝裕和透過一位剛剛失去摯愛丈夫的單身母親的視角,對失去親人和時光流逝進行了一次沉思。
《幻之光》(1995)
自60年代初小津安二郎逝世以來,西方影評人似乎一直在苦苦追尋小津電影詩學的接班人——終於,他出現了。「是枝」成為了新的「小津」。
兩人的相似之處在於——將對世俗的沉思,轉化為更超然的東西;在世界現代化和傳統不斷變化的背景下,對家庭紐帶的耐心凝視;或在最瑣碎的事情和無常的世界中,使事物運轉如常並尋求實質的天賦。
不過,是枝裕和對電影的理解還包括對系統性權力的批判,這是小津的作品所不具備的。
儘管是枝裕和的電影大都表現的是家庭戲劇,但它們也對構成家庭形象的主流敘事進行了聚焦和批判,挑戰了關於日本家庭關係的普遍理解,是枝也因此突出了自己作為一個疏離觀察者的立場。
此外,透過揭示日本家庭的不同形態,是枝對抗著同質社會的觀念,從而揭開了制度和家庭失敗的表象。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正是家庭構成了社會,併成為社會組織結構的主體。
正如是枝裕和在《如父如子》和《小偷家族》中所呈現的那樣,決定一個家庭存在與否的不僅僅是血緣關係。
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枝透過家庭的視角,對日本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試圖在現代語境中勾勒日本身份的軌跡,這與臺灣新電影大師侯孝賢的早期作品、楊德昌或大島渚的很多電影不謀而合——尤其是如果我們以騙局或借用身份等反覆出現的表現手法為參照的話。
《如父如子》(2013)
是枝裕和的最新作品《怪物》繼續勾勒出日本家庭承受系統性結構的壓力的背景,但這也許是他迄今為止最聳動的作品。
影片透過三個不同的視角,圍繞著小學生湊,他與母親、老師和學校環境的關係,以及他與朋友依裡之間的曖昧關係展開。
將敘事分解為不同視角的想法使是枝得以解開背景的特殊性——日本體制的框架,並在其中剖析了系統性的病理。
《怪物》(2023)
我們對影片的結構瞭解得越少,就越能沉浸在細膩的編劇(坂元裕二)和剪輯師(是枝裕和本人)合力精心製作的故事中。
我們踏上了一段旅程——穿插著故事中的故事、善意謊言或經不起推敲的敘事。這是一條充滿判斷陷阱的道路,也是關乎我們內心的道德探索,因為我們不斷質疑人物或其證詞的合法性。
「誰是怪物?」湊和依裡以嬉戲的方式唱出了這句詞,但真正的答案卻隱藏在影片所傳達的世代創傷之中。
我們與是枝裕和探討了他在《怪物》中講故事的方法、為故事尋找合適角度的過程、他與坂元裕二的合作(坂元裕二憑藉本片在戛納電影節獲最佳劇本獎)、日本的系統性怪物、與兒童演員合作的方法、如何透過剪輯保持節奏,以及對坂本龍一的記憶和他的音樂對影片的重要性。
問:這是自《幻之光》以來,你第一次拍攝不是由本人創作的劇本。我想這並不是坂元裕二給了你劇本就完事了,你需要對故事進行修改和調整,直到你覺得它符合你的要求。改編別人劇本的過程是怎樣的?
是枝裕和:的確,這並不是有人遞給我一個劇本,然後對我說:「來,拍這個!」的情況。我是在2018年12月接觸到這個故事的,隨後我們花了三年時間,在此期間,我們(與坂元裕二)來回交換意見,最終完成了劇本的成稿(初稿相當於三個小時片長)。
開始拍攝時,我覺得這和我自己寫劇本並沒有什麼不同。我非常投入地參與了寫作過程,從一開始就有一種設身處地的感覺;這種並非完全掌控的感覺反而更好,因為距離感會帶來某種便利。除此之外,我認為這種講故事的風格也不是我一個人能想出來的——事實上,我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
問:為什麼這麼說?
是枝裕和: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寫的故事都是生活片段。我關注的是某人生活中發生的某一連串事件,但我儘量不展示之前發生過或之後可能發生的事情。相反,我更依靠觀眾的想象力——我希望觀眾能夠敞開心扉,接受某些事情發生的可能性。這不是講故事;至少,我不會把它稱作講故事,因為在我創作的大部分場景中,我並不依賴於呈現的力量。
問:這在你與坂元裕二的合作中有什麼影響?
是枝裕和:坂元為我帶來了一些新的東西——一種真正的動力,一種讓故事繼續發展下去以探究下一步會發生什麼的動力。《怪物》少了我在之前的電影中所專注的刻畫生活片段的手法,而更多依仗於一些不同的東西——敘事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與坂元的合作是一次積極的經歷——在目前活躍於日本電影界的編劇中,他是我最尊敬的一位。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故事有著共同點——我們都在關注被忽視或拼湊的家庭,但以不同的風格來講述;就好像我們呼吸著同樣的空氣,撥出的氣體卻有些不同。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想和坂元一起拍攝一部電影,因為我無法像他那樣寫作。他改變基調和塑造多層次人物的能力一直是我所欣賞的,因為我覺得自己從不具備這種能力。
問:你的故事以往也曾涉及多個視角,但這一次,羅生門式的結構明顯帶來了故事中緊張氣氛的不斷升級。
是枝裕和:敘事的結構已經存在於情節中。這個想法直接來自於創作劇本的坂元。讀到初稿時,我的確辨認出了類似《羅生門》的結構。不過,我的想法並不侷限於三個不同的對比視角、三個真相。我想超越這一點,賦予兩位男孩擺脫這種結構的能力。在敘事的背景下,他們最終從這段關於追捕怪物的旅程中解脫了出來。
問:影片中有三個視角,但它們對應了不同的詞,雖然意思是一樣的——怪物。在每個部分,你都用了不同的詞來描述系統性怪物,分別是:monstā、bakemono、kaibutsu(日語片名)。
是枝裕和:這三個單詞在英語中的翻譯都是monster,對吧?
問:沒錯。
是枝裕和:這三個詞的含義幾乎相同,但也有些微差別。在日本,有一個詞用來形容糟糕的父母——「怪物父母」。大家都知道這個詞,所以老師才會在學校中使用「monstā」這個詞。還有一個在醫院裡的孩子,他在和媽媽的對話中使用了「bakemono」這個詞,在那種特殊情況下,孩子可能不會在與父母對話時使用「kaibutsu」。這三個詞彼此略有不同,它們帶來了微妙的差別,突出了不同的語境。但在翻譯時,我們不得不統一使用「monster」。
問:你的許多電影都深入探討了童年的主題,甚至很多影片的主人公都是孩子,而孩子的視角同樣充斥著親密性和主觀能動性。你似乎對孩童之間關係的特質非常敏感,特別是在《怪物》中,處理這一主題似乎需要一些勇氣。你是如何把握《怪物》的主題的?
是枝裕和:我認為這是一個確實需要勇氣去處理的主題。我自己對待這個故事的角度,是為了能夠從中獲益,學習其中的深意。我儘量充分地準備——我做了很多采訪,或與孩子們一起進行研討會。研究調查也非常重要。為此,我接觸了一些專家或參加了一些講座;我看了很多電影,從它們的表現手法中汲取經驗;我也深入學習了小學孩童的性發育、性表達和性認同等問題。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在故事的主題範圍內進行講述會有哪些危險。
從某種意義上說,表現令人不安或不舒服的事物很容易落入陷阱,因此有必要進行事先研究,以避免可能造成傷害的表現形式。當然,過多的研究也會帶來困擾,因此我必須謹慎選擇。總而言之,就影片要揭示的系統性怪物而言,我必須盡力讓孩子們在觀看時不會覺得不舒服,以免造成任何心理創傷。
問:鑑於你以前經常與小孩合作,我想知道此次為角色做準備的過程是否與以往一樣。
是枝裕和:通常,我不會直接把劇本交給孩子們。我往往會利用他們的個性來塑造他們身邊的角色。但這次的角色太複雜了,無法這樣做,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和孩子們討論角色。我也認為讓孩子們自己讀劇本的方法不適合這個故事,因為對白的風格不同,人物更加複雜。這就是為什麼我必須改變方法,讓孩子們能夠更好地掌握角色——儘管我嘗試了自己的慣用手法,但最終還是行不通。
根據劇本,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排練,就像與成年演員一起工作一樣。飾演兩個主角的小演員黑川想矢和柊木陽太,事先都反覆閱讀了臺詞,並且集中精力背了下來。我沒有強迫他們這樣做,但這對他們來說似乎是最有效的。
問:在拍攝現場,你對劇本進行的改動多嗎?
是枝裕和:我在拍攝自己的劇本時通常會採用這種工作方式——將修改意見列印出來,在拍攝現場分發給演員和工作人員。坂元瞭解了這一點之後,提出他自己也可以這樣工作。但我認為,如果突然在腦海中冒出一句新對白,可能會造成不必要的困難。如果有任何改動,我們會先與坂元討論,然後再應用到劇本中。在拍攝過程中,我偶爾也會想到些什麼——整個過程已經非常清晰,因為我根本不需要來回查閱自己寫作可能帶來的錯誤。這也非常有趣!
問:你也對學校和整體的學校環境進行了研究嗎?
是枝裕和:事實上,我自己也有教師資格證。20多歲的時候,我曾經當過老師,所以我透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瞭解到了學校系統的怪物性。我的很多朋友也是教師。事實上,我所認識的大部分與我同輩或稍年輕的人都是學校教師或在教育機構工作。在籌備這部電影時,我和他們聊了很多。這並不意味著整個故事的前提都是圍繞真實的呈現而展開的——其中也有一些虛構。
不過,我的想法是要體現學校政治的某種氛圍。儘管校長(田中裕子飾)這個角色看起來有點超脫現實,但我認為她在學校結構中的行事方式也可能真實地發生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事情需要大聲說出來。她的角色代表了對真理價值的信念的崩潰——這在一般社會機構中也經常發生,而不僅僅是在學校。
問:她也成為群體責任消解的集中代表。在母親(安藤櫻飾)與學校當局和老師對峙的「道歉場景」中,我們可以看到群體意識是如何表現的,其中學校代表之間的責任概念變得模糊不清。這看起來怪誕而離奇;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可怕的,因為個體行動的能動性被削弱了。你是否認為「群體主義」已經是對日本現代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的一大病灶?
是枝裕和:我確實認為,人們越來越多地公開批評群體主義心態。但是,在日本社會的許多方面,這是我們無法擺脫的。我們無從可避。在這部影片中,我的目的並不是單純地批判群體主義,而是要展示它的潛在可能性(也包括負面意義上的)。例如,母親只是想保護自己的兒子。當她用原本可能是用來欺辱她兒子的話——豬腦子這個詞——來反駁施虐者(老師)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人為了伸張正義會變成什麼樣。
我認為這種情況是真實存在的。群體心理也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它能演變成什麼程度。這部電影的某些內容可能看起來很不真實——無論是母親還是學校的行事方式。儘管如此,我並沒有用它來批評群體心理,而是想說明,由於群體心理在社會意識中依然根深蒂固,事情可以升級到何種程度。
問:儘管在劇本創作方法上存在差異,但你對時間和節奏的敏感度卻始終如一。你如何把握影片的這一方面?
是枝裕和:這一切都關乎於剪輯。我可能會根據其他人的劇本或攝影而調整合作方式,但有一件事我總是儘量自己上手,那就是剪輯——這是電影的節奏所在。因為電影是有生命的,它有心跳,「咚咚咚」。關於電影節奏的把握,有很多門道。但與之相輔相成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場面排程。跟上場景的節奏,就像創作音樂一樣。指揮家的工作就是保持正確的節奏;電影導演也是一樣,我們的工作就是保持電影的節奏,而這可以透過剪輯來實現。
問:如今,《怪物》也可以看作是對已故的坂本龍一的紀念,你與他是第一次合作。影片的大部分配樂來自於他的最後一張專輯《12》——我感覺這張專輯中的音樂能讓人完全感受到故事裡蘊含的憂傷。我聽說你經常一邊聽他的音樂一邊寫劇本。這次影片的氛圍是否與他的作品有些關聯?
是枝裕和:這次有點不同,因為我不是自己寫的故事,所以沒有腦海中響起音樂這回事。但當我們開始拍攝和後來剪輯影片時,我一直在聽坂本龍一的鋼琴曲。可以說,如果沒有他的音樂,我就無法完成這部電影。我想,如果不是他願意參與這個專案(最終貢獻了兩首新曲子和《12》中的許多曲目),我可能不得不改變影片的方向。這是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合作,我永遠感激它最終成真。
#坂本龍一名曲 #坂本龍一兒子 #坂本龍一代表作 #坂本龍一久石讓 #坂本龍一空里香 #坂本龍一去世 #坂本龍一香港 #坂本龍一死因







.jpg?w=1200&resize=1200,0&ssl=1)